群租客講述在京生活 來了一年一分錢都沒攢下(3)
“北京的生活壓力太大,我們班當初一起來的30個同學,如今隻剩三四個。”第一次來北京實習時,彭慧就見識了首都的包羅萬象。
彼時的她在中國美術館實習,做服務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告知遊客不要碰畫、不要吃東西喝水。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5點,站兩個小時休息半個小時。包吃包住,每個月拿到1900元補貼。
彭慧回憶,從沒見過那麼慘的“包吃包住。“她和另外17個人住在一間40平方米的地下室。正值北京的冬天,地下室裏沒有暖氣,也沒有熱水。大概是由於不習慣北京的自來水水質,彭慧的臉上開始冒痘痘,“當時的條件又隻能用冷水洗臉,那時候滿臉痘特別不想見人,醜死了。”
大部分時候,彭慧需要掰著手指算錢過日子。在交完所有費用之後,彭慧的手裏隻剩800塊錢,公司在最初的一個月不發工資,她需要用這些錢過完兩個月。公司隻提供午餐和晚餐。彭慧從來不吃公司的菜,隻吃米飯。有時去早市買些鹹菜,就著米飯一起吃。晚上的時候彭慧從食堂拿兩個饅頭,花10塊錢買一盒8個的鹹鴨蛋,還有老幹媽辣醬。晚上1個饅頭、半個鹹鴨蛋,剩下的留到第二天早上當早飯。“如果實在忍不住,頭天晚上吃了一整個鹹鴨蛋,那第二天早上就不吃了。”第二天早上的饅頭一咬一掉渣,彭慧就著辣醬,喝著水,大口大口地往下咽。後來發工資了,彭慧想要改善一下夥食,買了個煎餅果子,還有“雙夾”——一種夾了雞蛋和火腿的餅。
彭慧不願意回憶起當初的苦日子,對未來也沒有顯出一籌莫展。辭掉工作後,她正在網上投簡曆、找工作。目標是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工資可以比以前低點。“頭疼死了,毫無頭緒,想找個文職類的助理工作,但自己辦公軟件什麼的又不太在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但公司不給交五險一金,別的倒無所謂,醫保一定要交啊。”彭慧有時覺得,實在不行就繼續做銷售,畢竟是熟悉的領域,但是自己又沒有本科的學曆,她對於找工作略顯迷茫和無能為力。
彭慧有時會羨慕一個同學的舅舅,70後,多年前兩手空空來到北京,沒有學曆,隻有吃苦耐勞的勁兒。“當時他剛結婚,還要養孩子,一個月工資幾百塊。就靠自己一步步奮鬥,現在在北京有房有車,還有自己的公司。”彭慧覺得自己現在拚不過“富二代”,也不指望在北京買上房。“北京隻適合掙錢,不適合居住。3年之後,我和對象賺足了錢就在老家買房,長遠的打算還是回家。”彭慧說自己在學校時從來沒有想過這些複雜的問題,每天過得很開心。工作之後,學著生存,這些問題遲早會找上門來。
“隻為活著一點生活質量都沒有”
李可很少對這座城市投入感情。在這間群租房裏她總是顯得焦躁而憤怒,與這裏居住的醫院護士、來京實習大學生、推銷銀行信用卡的職員不同,李可在北京已經工作了三四年,自稱是培訓學校的副校長。
因為進進出出的人太多,群租房的門鎖並不好用,姑娘們每次出門前都要仔細檢查幾遍有沒有帶鑰匙。因為如果沒帶鑰匙,敲門是沒人會來開的——“有人敲門時,×姐不讓我們開門。”姑娘們口中的“×姐”是這裏的房東或是二房東,租客們也不知道×姐是不是這棟房子的實際擁有者,她們與她的聯係是每個月定時交房租和房間裏有東西壞了時,打電話給×姐,她會派人來修。×姐也不允許代收快遞,習慣網購的年輕人隻能自己在家的時候讓快遞來送。
不久前,這間房子剛剛被人舉報過。在電梯裏也時常有鄰居向租客們打聽房間裏是不是住了很多人,租客們往往諱莫如深。令她們頭疼的還有小區的大門口,由於需要刷卡進入,沒有卡的租客們,隻能等著別人進出的時候跟在後麵。“人多的時間段還好,可是有時候人少,遠遠看到前麵有一個人要進去或者裏麵有人出來,我都要急匆匆跑過去,趁門開了跑進去,有時候實在裏外都沒人就隻好等著,那種感覺一分鍾都像是過了一個小時。”一位租客說,“為了掩飾尷尬,我通常拿出手機來玩兒。”
晚上大家下班回來,洗衣服做飯洗漱聊天,群租房內開始進入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光,李可嫌吵,直接在客廳貼了張告示——晚上9點以後不準在客廳聊天說話,可是這似乎並不奏效。晚上11點之後,洗澡聲、馬桶衝水聲、洗衣機轉動聲、打電話聊微信聲不絕於耳。有人熬夜工作不肯關燈,連帶著劈裏啪啦敲擊鍵盤的聲音。有一次,李可在衛生間裏洗澡,有人進來上廁所,出去的時候沒有關門,讓她著了涼。為此,李可差點與那人大打出手。
盡管時常帶著憤怒,李可還是不願意搬走,她曾有過複雜又曲折的租房經曆。“被中介騙過、遇到過難纏的房東、因為工作調動為找新房子急得團團轉......”
“租房市場中存在的一係列侵權問題已給青年人才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廉思說。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者中,僅有26.3%的人表示在租房過程中未遇到權益受損問題,33.3%的人表示自己曾經遭遇房東臨時清退,且無補償,41.3%的人表示自己曾遇到租金不按合同隨意上漲的情況,更有43.8%的人表示自己曾遭遇過黑中介克扣甚至騙取中介費。
李可的同事有在燕郊買房子的,“上下班要兩個多小時。”李可在一周一天的休息日整理著衣服,“隻為活著,一點生活質量都沒有。”她將疊好的衣服放進旅行箱,群租房內沒有衣櫃,李可就準備了4個旅行箱,一個大過一個。高低床的一角掛了5個包。
李可說自己的目標還沒有完成,所以不能離開北京。“自己當老板,開培訓機構,這隻是小的目標。”春天的柳絮飄進了屋子裏,李可抓了抓,卻沒抓住。一同飄進來的還有不遠處北京站的整點報時鍾聲。“大的目標,現在還不能說。”李可補充道。
這個畢業於東北財經大學的高才生曾經在通州租過一居室,每月租金2000元,占李可當時收入的五分之一。“晚上下班特別晚,通州的大馬路上沒有人,遠遠的突然走過來一個,像幽靈一樣,特別嚇人。”
“每天上班幹嗎?掙錢買房子。買房子幹嗎?還房貸。”李可說很多人的生活進入了惡性循環。她覺得這座城市過於功利,在嫌棄的同時,自己也成了它功利的一部分。所有的意義就變成“討生活”3個字。
“回家鄉才是拚爹,在這裏更公平”
盡管有各種牢騷,但群租客們依然對北京以及自己的未來抱有希望、懷有願景。
在一套群租房的6人間裏,住了4個河北姑娘和兩個甘肅姑娘,“五一”小長假結束後的第一個晚上,這間並不寬敞的屋子裏笑聲不斷。來實習的蘭州大學的女孩們就要結束實習離開北京了,剩下的人為她們舉辦了一場小小的歡送會,幾瓶啤酒,幾碟小菜,聊天就是這場歡送會的全部內容。
跟房子裏其他租戶的形同陌路不同,在來自河北的趙爽所住的6人間裏,大家一直相處得很愉快。總說要搬走,可是因為太忙了,沒空找房子。就是晚上回來睡個覺,所以沒搬走。在她看來現在住的地方挺方便,“一塊住的人這麼多,大家生活習慣都不一樣,就是個互相遷就唄。”
現在,6人間裏隻剩下趙爽和張萌兩個人了,張萌是醫院護士,不經常回來。“再過幾個月,如果能找到合適的房子,我打算跟張萌搬出去合租,不再住群租房了。”趙爽說,“群租早晚有一天是要被取締的,我也讚成取締群租。可是現在大家掙得不多,北京房租又貴,那還能怎麼辦?一塊租房可以,做成那種宿舍式的管理可能好一點。”
趙爽去年3月還沒畢業就隻身來到了北京,會計專業的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會計。因為“太安逸了,每天都沒事幹,就是坐著刷網頁聊QQ”,所以今年年初,趙爽選擇了跳槽,現在她在一家證券公司謀得了一份後台谘詢的工作。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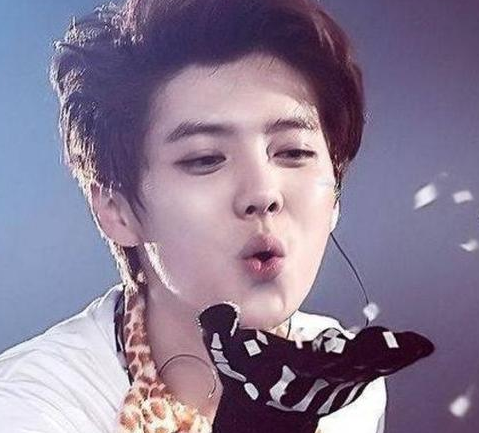


















 粵公網安備 44140302000013號
粵公網安備 441403020000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