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閉症怎麼會等於傻 救救那些孤獨的孩子

曾經熱衷於當誌願者的我,也熱衷於和其他誌願者交流。誌願者幫助別人,自己也獲得慰藉。雖然誌願的場景不總是美好的,更多時候甚至令人膽寒,但老人會仙去,孤兒會長大,很多苦難都會有終點。
但服務於自閉症(亦稱“孤獨症”)患者不是這樣。你無法從他們那獲得慰藉,你與他們越近,感覺距離就越遠。你工作的時間越長,接觸的自閉症患者越多,就感覺自己越孤獨,而他們甚至比你更孤獨。最關鍵的是,這種孤獨也許永遠也沒有盡頭。
寂靜者的哭號
我來到朝陽區殘聯的時候,整座大樓靜得可怕。馬先生告訴我,除了四層,這裏平時人不算多。
果然,邁出電梯進入四層時,一波波聲浪開始衝擊我的耳膜:幼童的哭鬧,中年人的訓導,年輕女性的嗬護,還有不知來自什麼人的無窮無盡的低語。我環顧四周,地上全是孩子,東奔西走的全是老師,而在椅子上垂著頭坐著的全是家長。
用門可羅雀來形容殘聯平時的樣子絕不過分。但是這區區一層裏停留了將近100……不,大概將近200人。彼時正是周三下午,在座的家長們普遍也就30歲左右,這令我不禁擔憂起他們的考勤。
這是屬於自閉症兒童的地帶,在殘聯一隅的自閉症康複機構——五彩鹿。這裏相當吵鬧,但空氣中充滿了壓抑。這裏從不缺人,卻遠離世間關注,甚至連拍照也被列入禁止行列。父母們不希望高調地讓孩子接受自閉症幹預,這種病成了語言上的禁忌,雖然它在社交媒體上那麼頻繁地出現,但鮮少有人願意跳出來把自己當成標本。
一個孩子在被老師反複地詢問:「你剛才喝水了嗎?你有沒有喝水?剛才是喝水的時間,應該去喝水呀?」隨後,這孩子什麼話也沒說,拿起水杯準備再喝一口,直到被他的同學打斷——一個看上去還算開朗的小男孩怯生生地說:「老師,我看見他剛才喝水了。」老師耐心地繼續詢問:「喝水了呀?喝過了為什麼不說呢?」這就是自閉症兒童常見的狀態之一。如果說部分平常人缺乏社交技巧,自閉症患者則根本缺乏社交的意願和能力。他寧願再去喝一次水,也沒辦法告訴老師「我喝過了」。
我們穿行於不同的教室,穿行於集體輔導區和個別輔導區。「這個桃子好吃,你喜歡嗎,想要嗎?」「現在你拚完了,是不是應該把拚圖還給我呀?」諸如此類最基本的社交引導,每個老師都在不斷地重複。這讓我想起某個經典的自閉症幹預場景:為了讓自閉症兒童知道「名字」的含義,老師每次喊他的名字,就跑到他身後,替他答應;再跑回來,繼續呼喚,再跑到身後。這樣重複幾百次、幾千次。
馬先生帶我到一位教職工身邊。這個年輕人安靜地坐在角落裏裁剪彩紙,我們湊近時沒有任何反應。馬先生喚他,向他介紹我,他對我說:「你好。」馬先生問他:「你在做什麼?」他說:「我在製作教具。」我們從這間教室出來,馬先生說:「幹預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一定適用於每個個體。我們的目標是讓自閉症患者能夠融入社會,或者至少能獨自謀生。雖然並不是所有患者都能做到。」「像他那樣的,隻是少數。」馬先生回望裁剪教具的青年職工。
靈魂的10%
相比美國和日本,中國的自閉症幹預事業起步算比較晚的。1982年(美國早在1943年便確診)中國內地確診第一例自閉症患者,90年代起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楊曉玲等數位專家開始研究時,手中僅有30個病例。93年起,星星雨等民辦康複機構才陸續成立,自閉症家庭才陸續有了「去處」,即便很多時候隻能尋求慰藉。
在這之後,直到2006年,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才參考國際標準,將自閉症納入精神殘疾範疇。而知名醫院支持的大型機構,比如北大醫療兒童發展中心,你猜是哪年才成立的?答案是2015年。別忘了它僅僅位於北京而已。
朝陽區殘聯四層的這家康複機構名為五彩鹿,是國內最大的相關機構之一,成立於2005年,聽上去是家「有年頭的企業」了。但鑒於行業的特殊性,對比於今日互聯網企業成長的速度,五彩鹿被稱作創業企業也毫不為過。
五彩鹿創始人孫夢麟的前一份工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家庭主婦」。由於家庭環境比較寬裕,孫夢麟旅居日本、加拿大多年,兒子初中時她倆已走遍數十個國家。在從事誌願工作的過程中,孫夢麟結識了北醫六院的自閉症專家楊曉玲教授,並逐漸走入這個圈子,最終於2005年成立五彩鹿。
彼時的孫夢麟,可以說除了時間和錢,什麼都沒有。中國的自閉症人才本來就少,如楊曉玲等專家雖然願意給五彩鹿提供有限的支持,總不能全身心投入一家創業公司。在這種連方向都摸不著的環境裏,五彩鹿該怎樣起步呢?用孫夢麟的話說,她「運氣很好」,趕上了兩個會議。這兩個會議使她遇到了必需的合夥人,和最初的客戶。
2005年年底,第三屆國際行為分析協會年會(ABAInternational)在北京召開(03和04年分別在意大利和巴西)。「行為分析」(即ABA)與自閉症診斷、幹預有莫大的關係,孫夢麟便在會上遇到了日後給五彩鹿帶來了莫大幫助的以色列ABA專家伊坦·艾德博士。也是在這幾天裏,孫夢麟結識了美國皇後學院的王培實教授。
艾德博士是以色列ABA協會第一任主席,有自己的研究機構,領導著一個自閉症康複訓練專業團隊。而王培實教授則在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皇後學院就職,是博士級應用行為分析治療師。二人對自閉症治療的社會價值頗有體會,學術研究方麵也正在渴求來自中國自閉症群體的巨量數據。他們與孫夢麟一拍即合。
不過,讓他們投身中國的創業公司,總要付出點代價。艾德便開出了相當高的條件,比如10000美元的月薪(在05年絕不算低),比如吃住五星酒店並由公司報銷,還比如艾德要拿到公司全部收入的10%。
天呐。
注意,是收入的10%,而非利潤的10%,是income而不是net income。如果答應這一條件,那意味著艾德才是真正的老板,包括孫夢麟在內的整個五彩鹿都將為他打工。
然而孫夢麟最終還是與艾德簽訂了為期三年的合同,條款包括「收入的10%」。事實證明孫夢麟的決定是正確的,艾德不僅為五彩鹿奠定了科學的診療方法,培養了本地人才,也為五彩鹿建立了龐大的自閉症病例數據庫。這一數據庫令國際學術界刮目相看,也令五彩鹿成為世界自閉症研究的領軍者。

然而,在艾德入職之初,作為一家創立不久的企業,五彩鹿是怎麼撐下來的?
巫術、商業與科學
家長在正規機構為自閉症兒童尋求「出路」時,聽到的第一句話往往就是「自閉症目前無法治愈」。
與常見的誤解不同,自閉症並非抑鬱症和焦慮症,大多情況下不需要吃藥,但也缺少治愈方法。正如馬先生所說,「目標是讓自閉症患者能夠融入社會,或者至少能獨自謀生」,而並非「一勞永逸」。絕對不要因為「不能治愈」就認為早期幹預無關痛癢,科學的幹預可以改變自閉症孩子的一生,讓他們「更有質量」地和普通人生活在一起。
即便如此,很多家長最初參與治療時,仍然抱著一勞永逸的心態。因此,一些自閉症幹預從業者覺得最難溝通的不是患兒,而是家長。
不過,讓家長崩潰的不僅是無法治愈的尷尬,還有高昂的治療費用。在美國,自閉症幹預教育1年的費用為7萬到12萬美元,遠超大學學費,一般家庭根本無力負擔。五彩鹿提供的專業治療雖然比美國便宜得多,考慮到中國家長的收入,仍然是個沉重的壓力。
但孩子的事兒比天還大,這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上文提到的兩個會議,第二個便是在廣州舉行的某次非正式會麵,有很多自閉症患兒家長到場。彼時五彩鹿剛剛成立不久,卻是中國罕有的自閉症康複機構之一,很多家長聽聞五彩鹿後,便馬上找到孫夢麟預約。他們從廣州北上,前往北京接受治療,與北醫六院各位專家推薦的患者一起,構成了五彩鹿的「種子客戶」。
成立一年,一個會議帶來了王培實和艾德,一個會議帶來了大量種子客戶。孫夢麟說:「我覺得這兩個會議就是為我們開的。」但隨後,孫夢麟馬上發現自己多慮了。在幾乎未做市場營銷的情況下,五彩鹿的康複場地12年來比肩繼踵,其背後原因十分簡單也十分殘酷——不僅中國,全世界範圍內的自閉症康複機構都太少了。
我確實在殘聯四層看到了很多白人兒童和白人父母。客觀來講,號稱提供自閉症治療服務的機構在世界各地絕不算少,然而它們又都是些什麼東西呢?
許多年來,許多家長帶著自閉症孩子去做開顱手術,手術做了三四次,孩子罪沒少受,自閉症一點也不會好轉。孫夢麟無奈地表示來到五彩鹿的孩子也有不少曾經做過開顱手術,這源於家長的心急如焚和無良機構的騙誘。
然而開顱也不隻是愚昧的全部。媒體關於自閉症的報道是血淋淋的。有些機構為了糾正自閉症兒童的刻板行為,采用暴力毆打,使其變成「不敢說話不敢動」的木頭人,並自居成功。有些機構認為自閉症兒童精力旺盛,令其穿上棉衣跑步,在孩子累到虛脫後自稱「使患兒安靜了下來」。至於各種電擊倒吊紮針灌藥,更是不勝枚舉。
當然有孩子在非人的治療過程中死去,然而違法機構即便被取締,也並未給患兒及家長帶來新的希望。即便在正規機構,無法治愈、漫長療程和高昂費用也在摧殘著家長的心。
自閉症患兒經常出現症狀的反複,這使得教育者的成就感屢屢受挫。跳到孩子背後10000次,也許使他記住了自己的名字。但有一天早上醒來,你再喚他時,他的反應可能突然就像一年前一樣了。患兒可以原地踏步,家長又怎可能回到1年前的心態,怎可能將這1年時光當作虛無?
在開始治療孩子的自閉症以後,許多家長不約而同地產生了一個念頭:「我要離婚。我怎麼和他/她生出了這麼一個玩意兒。」這話聽著可怕,比這更可怕的卻還有的是。2016年春節前夕,湖北的一位父親勒死了自己5歲的自閉症兒子,然後自首。他痛哭流涕,他全家都痛哭流涕,然而孩子已經被他埋到土裏去了。
自閉症對患者家屬的摧殘是現實的、不可忽視的。正規的幹預機構不僅需要對自閉症兒童開展多種課程,也不會忘記對家長心理健康的輔導。如果家長不上心、不配合,僅憑老師很難達成治療目標。
我在五彩鹿見到了一位體型巨大的小胖子。他的自閉症久治不愈,被父母拋棄,與爺爺奶奶住在一起。老人的家教水平對自閉症幹預是無能為力的,孩子的狀況便時常反複。即便老師們親密陪伴,每天與他睡在一起,得來的也隻是遭受攻擊的抓痕而已。這位患兒的刻板行為體現為暴食,這令他的外表看上去就「不太正常」——其實,在被父母拋棄之前,他並不肥胖。
誰知道等待他的又是什麼未來呢?在瞎治、亂治以外,正規機構施行的正規治療,也會在投入不足時收效甚微。五彩鹿在北京的四個校區——順義、安貞、天通苑和高碑店每日人滿為患,每年幾乎為一萬患者提供服務;相對於排隊上課而不得的患者,「10000」隻是杯水車薪。
孫夢麟算了這麼一筆賬:自閉症教師上崗,首先需要專業對口,然後要進行兩個月的脫產培訓。脫產培訓後,還要大概一年的實操,才能獨立上崗,創造效益。教育自閉症兒童,工作內容繁重,心理壓力巨大,卻並不是光鮮的、社會地位高的職業。相比於教鋼琴、教畫畫的藝術類教師,他們收入也絕不算高。
孫夢麟說,如果想從根本上為廣大自閉症患者提供充足的醫療支援,就必須提高從業人員的待遇。這也是五彩鹿的長遠目標之一。因此,很容易理解,在自閉症幹預領域,頗負盛名的星星雨即便成立較早,但NGO能承擔的責任是十分有限的。
作為企業的五彩鹿,12年間能自給自足地開辦四家校區,治療十多萬患者,足以證明該領域蘊含的商業價值。想扭轉自閉症治療供需極度不均的局麵,商業化是必經之途,這也是五彩鹿近兩年像一家「創業企業」般開始融資的原因之一。實際上,早有互聯網圈投資人涉足自閉症相關項目,「恩啟雲課堂」就是成果之一。

人造禍患
在漫長的醫學曆史中,自閉症發病率一度被認為隻有萬分之二到萬分之四,屬於罕見病。
然而這已是20年前的結論。
跳過觸目驚心的增長曆史。2016年,美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美國自閉症發病率已高達1/68,而中國按照最保守估計也有1%的發病率。即是說中國現存至少1000萬以上的自閉症個體,其中14歲以下的兒童就有200萬。這意味著自閉症已經不再屬於罕見病,成為了普遍的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並非意味著自閉症的「發病率」快速增長,很可能隻是「發現率」大幅提高。中國人的科學育兒意識在最近10年才開始爆發,早教課程相對普及也不過是5、6年;若沒有家長的知識儲備及警惕心理,自閉症的「確診」實屬不易。我們可以想象,曾經的無數患兒,隻是被家長和社會當作「瘋子」「傻子」對待,尤其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
十多年前,電視節目中偶爾出現被爹媽用鐵鏈拴在家裏的孩子。雖然無法驗證,但他們很有可能就是重度自閉症的受害者,隻不過當時其身邊人對此毫無知覺,社會大眾更僅僅是把他們當作獵奇的談資。
今天的狀況當然好一些,但大多數父母仍然不具備正確的態度,整個社會對自閉症充滿了誤會。
舉例說明第一個錯誤——我們現在激增的自閉症案例都是怎麼發現的?當然有少數非常認真負責的家長能在孩子幾個月大、或至少3歲前發現孩子的異常,但更多家長對自閉症的察覺是非常被動的。具體表現為:當他們的孩子該上幼兒園時無法上幼兒園(通不過麵試,或者被勒令退學)、該上小學時無法上小學,他們才會意識到「我的孩子有問題」。這令我想起《浪客行》中鍾卷自齋養育小次郎的故事:都養出感情來了,還沒發現這孩子是聾的。
簡而言之,家長希望孩子「在正確的時機做正確的事情」;即便帶著孩子參與治療,也隻是希望孩子將來「該上中學時能上中學、該工作時能賺錢」。這種樸素的願望無可厚非,但自閉症幹預的黃金時間是8歲以前,14歲之後的幹預已經基本沒什麼用了。主動發現越早,對治療越有利,而這種「被動的發現」不知耽誤了多少人。
照理說,自閉症是先天性的,即便被動,即便後知後覺,孩子的異常也應該在幼兒園入學時就可以發現。之所以仍有太多人被耽誤,一是因為病情有輕有重,有的孩子直到中學階段的異常才嚴重影響其學習、生活;二則是因為,許多國人忌諱這種病症,即便發現了也常常抱有「僥幸心理」而試圖拖延,最終釀成惡果。
這便是第二個錯誤。就像「被鐵鏈鎖住的孩子」一樣,假如家長煞有介事地帶著孩子求醫問藥,親屬和鄰裏便會風起流言:「那誰家生了個傻子!」這種壓力無疑會令患者家庭更快崩潰。在朝陽區殘聯四層,我見到的很多家長都是「背著家裏人來的」,尤其是「背著爺爺奶奶來的」,因為他們無法再承受家人的詰問。
自閉症怎麼會等於傻?在外貌上,自閉症患兒與唐氏綜合征(或說21-三體綜合征,很多人應該在生物課本上見到過)患兒區別明顯,根本不該將其混為一談。然而,正常的外貌使得自閉症更難被診斷,真不知道這算好事還是壞事。
同理,雖然自閉症被國家視為精神殘疾,並且有月度補助2600元,但真正會去領取這2600元的家長並不多,因為領取的前提是辦理殘疾證。用一位家長的話說:一旦辦了殘疾證,無疑是在自閉症之上更添一道「終身創傷」。他們不願讓孩子自視「殘疾人」。
第三個錯誤體現在「自閉症都是天才」等刻板印象上。經常有人將自閉症與亞斯伯格綜合征等而論之。亞斯伯格綜合征是自閉症中表現較輕的一類,雖然同樣伴隨社交障礙、沉默寡言和刻板行為,但並不帶來智力障礙和語言障礙。患兒往往可以作為一個「有些古怪」的人在社會上立足,有些甚至能成大器,比如漫畫家朱德庸。
但這不等於亞斯伯格綜合征是「天才病」,事實上更多患兒隻是飽受折磨而已,而八成的自閉症患者程度比亞斯伯格綜合征重得多,他們的問題不僅在社交上。對於這部分患者,「能成才」大概是幻想,「能獨立謀生」已經是治療的最高目標;而對於少部分病情更危急、智力表現更差的重度自閉症患者,治療目標隻得降低為「能生活自理」。
第四個錯誤則是家長的繁忙。上文提到過,由於老師不可能時刻伴隨患兒,家庭教育中的幹預就成了重中之重,這要求父母抽出足夠多的時間精力去陪伴孩子——這對中國工薪族而言幾近奢談。隨著患兒被丟給保姆和爺爺奶奶,患兒的人生前途也就愈發黯淡。
然而父母不應被責備,這種病痛本應受整個社會支援。自閉症是病,衛生部門該管;自閉症的治療之道是教育,教育部門該管;自閉症是精神殘疾,殘聯該管;自閉症引發諸多社會問題,民政局也該管。但以目前的狀況來說,整個社會對自閉症的關注與支持還遠遠不夠;毋寧說,相比於關注和支持,誤解和傷害還要普遍得、深刻得多了。
孫夢麟12年來奔走於國內外,在醫生、學者、誌願者和官員之間建立共識。他們爭取到殘聯的場地,爭取到在各大協會的發言權。如果正確的觀念不被傳播,就還會有患兒遭受無意義的開顱,還會有「瘋子」被像狗一樣拴在農村的院子裏。
作為康複機構,五彩鹿12年間治療的十多萬患者早已成就了全球最大的自閉症病例數據庫,這使他們在學術界名聲斐然。他們從去年起廣結良緣,招收技術人才,希望用「平台」的形式,將事業從線下拓展到線上:從自閉症兒童早期幹預,發展到包括對家長遠程指導的「全家庭支持」,再到對自閉症患者生命的「全程支持」,即是說補完「對成年自閉症患者的救助」。
他們要提高教師的待遇,要糾正家長的觀念;他們要盡力覆蓋病童,也要思考對成年自閉症患者的關注;他們在試圖走出北京,也試圖走向國外……我對孫夢麟說:這些聽上去不像是一家企業能完成的。馬先生補充道:即便是目前的所有從業者加起來,也還遠遠不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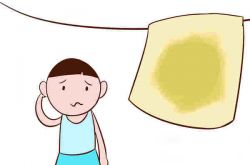





















 粵公網安備 44140302000013號
粵公網安備 441403020000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