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琦:從國際視野,看中美共同的曆史
徐國琦,安徽樅陽人。哈佛大學曆史係博士,現為香港大學曆史係教授。主要著作有“國際史”三部曲:《中國與大戰》(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中文版);《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2008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戰中的華工》(哈佛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其英文版,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目前正致力於其“共享曆史”三部曲的寫作及研究:《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享的曆史》(已完成。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14年9月出版該書的英文版,廣西師大出版社擬出版其中文版);目前正撰寫《亞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個共享的旅程》(該書係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約稿,英文書稿當於2015年中旬完成);其第三部《關於中國:一個共享的曆史》仍在研究之中。
前不久,徐國琦的著作《邊緣人偶記》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徐國琦在外研書店就此舉辦講座,鳳凰網專訪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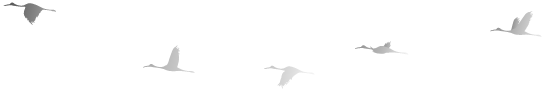
高見
關於中美關係,我此前讀過唐啟華的著作,裏麵有一點涉及中美外交,當時威爾遜對中國很友善。
徐國琦:中美外交,2014年我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了一本書,闡述的就是中國人跟美國人的一個共有曆史。我們現在看的是中美之間不同等級對抗,實際上曆史上來看,美國之所以獨立,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它要到中國市場來。
因為當時美國作為大英帝國殖民地,大英帝國壟斷了中國的貿易,美國十三州殖民地的人第一要直接到中國貿易,所以1784年跟英國脫離,獨立之後,“中國皇後號”就來了中國。
第二,美國獨立時,1763年所謂波士頓茶黨事件,當時美國人對英國不滿,波士頓傾茶案,它那個茶是中國的茶,所以一開始這個裏麵就都有聯係。
另外就像美國準備獨立的時候,美國國父富蘭克林,他當時想,美國獨立之後,要接受中國的儒家文明,富蘭克林說儒家文明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文明。
當有人告訴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中國人不是白人的時候,他大吃一驚。他覺得中國人就是白人,這麼厲害。

高見
在唐啟華的著作中,威爾遜的主張大大激勵了中國人,他的聲望在中國很高。您怎麼看?
徐國琦:我們的研究有一點交叉,但觀點不完全一致。1914年到1918年的一戰對中國來說是承前啟後,非常重要。
1912年,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為什麼他要學習法國和美國,變成民國?你要看孫中山的內閣、袁世凱的內閣大部分是留學的學生,如外交官顧維鈞是留美博士,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是留美幼童,袁世凱的心腹大員蔡廷幹也是留美人士。在內閣成員裏麵,留美背景極強,中國人當時就是要更新換代,要學習美國。

清末第一批幼童三十名赴美留學於同治十一年(1872)攝於香港。
一戰爆發後,1917年8月14號,中國呼應美國,對德奧宣戰。因為當時威爾遜作為中立國總統,呼籲全世界中立國仿效美國,而中國一直就想參戰,正好等這個機會趁勢而起。
所以,威爾遜當時發表十四點,民族自覺、平等外交等等,對中國人來說,那是天大的好事。正因為如此,威爾遜當時在中國被年輕人視為上帝,中國留學生到美國領館去呼喊“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在他的一篇文章公開稱威爾遜是世界上頭號好人。毛澤東那時候還名不見傳的,但是他也發表了一些文章,就想未來的中國跟美國如果是同盟,那所向披靡。當時的年輕人有一個很強的親美情節。威爾遜當時所謂的新國際秩序對中國非常有誘惑力。

高見
關於蒲安臣,大多數中國讀者不是特別熟悉。
徐國琦:1868年,中國第一個出使世界的使團的團長是美國人蒲安臣。他這個人非常好,1861年到1867年是美國對華公使,1867年他準備回國的時候,中國的總理衙門說,你能不能代表我們出使全世界,他答應了。
所以,1868年中美之間第一個和平條約、平等條約是蒲安臣代中國簽的。蒲安臣條約為什麼平等?第一個它講究中美兩國人民可以自由來往,自由移民、自由來往、自由求學。

蒲安臣是1868年代表中國,先到美國華盛頓跟他的前領導William Henry Seward(西華德)國務卿簽的這個條約,然後就到英國、到法國、到德國,然後1870年死在俄國,死的時候49歲,是中國政府的外交官,中國政府的雇員。蒲安臣的墓就在與哈佛大學咫尺之遙的奧本山墓地,錢是中國人出的。
在這些例子中,中美之間沒有對抗,當時中國人和美國人互相吸引、互相坦誠,另外也互相支持。

高見
上世紀,另外一個美國人約翰·杜威對中國影響也很大,胡適、馮友蘭都是他的弟子。
徐國琦:另外,杜威的學生還有蔣廷黻、蔣夢麟、陶行知等,民國期間都是各方麵的領袖。約翰·杜威1919年4月30號到中國,一直到1921年7月份才離開。因為杜威在中國這兩年,對他自己的影響也很大。回到美國之後,他儼然變成了中國專家。1952年,杜威過世,1945年時他都還想到中國來調停國共。

高見
齊錫生、楊天石老師的書裏麵也有講到,抗戰時期,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對中國比較友善,而蔣介石為何特別厭惡丘吉爾?
徐國琦:中國在一戰是極貧極弱的,沒人理。二戰是美國總統羅斯福堅持,使得二戰之後中國成為四大戰勝國之一。當時大英帝國丘吉爾竭力反對,斯大林竭力反對,而美國堅持。
因為美國人的堅持,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強之一,蔣介石當時自己都覺得這個地位變化太大了。一戰時,中國是一個極貧極弱的國家,任人宰割,到二戰成為四強之一。之所以如此,因為當時美國人不喜歡法國人,法國後來是五強。從中美關係看,這個是剪不斷的關聯,況且很多方麵都是正麵的。

高見
因為你是從中國到美國再從美國到中國,從個人的思想史角度來說,你對美國的認識過程是怎樣的?
徐國琦:第一,要從中國近代曆史上看,最早的留學浪潮是中國官方組織的留美幼童。1872年,當時的美國實際上無論從哪個角度應該說不是首選,因為美國高校比不上歐洲,當時最好的高校在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當時的哈佛大學不過是一個小的、不入流的學校。而中國的留美幼童都送到美國去。
1872年留美幼童前往美國,1881年召回,120個人。比如說第一任民國總理唐紹儀,設計京張鐵路的詹天佑。剛才我說的蔡廷幹也是。留下的一百多人,人人都是各行精英,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美國當時也是個弱國、窮國,因為1872年美國剛剛結束了內戰,正在重建,政治不穩,經濟落後,高校也不發達。但就在那種情況下,因為中國人對美國人一種天然的好感和信賴,就派過去。這是第一波留學浪潮。
美國一戰時成為世界強國,二戰後成為世界霸主。隨著地位上漲,美國對中國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我個人看,過去中國人有幾個誤區,就認為中國是文明古國,美國好像是中國的小老弟,但你反過頭來看,美國是世界上有成文憲法最早的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有共和國機製最早的一個,美國、法國。中國是1912年才有的。

高見
就你講的這些,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庚款的退還。我看到特朗普在聯合國的演講,他說美國是向善的主要力量之一。這一點,您怎麼看?
徐國琦:你說的退庚款也是美國人最先。1904至1905年間,梁誠曾敦促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減免部分未付足的庚子賠款。他勸說美國政府,當年庚款要的太多了,遠遠的超過實際需要,多餘的要退回來,美國人接受了。
在所有的列強裏麵,美國是第一個。後來其他國家在各種壓力下也開始退,但是不了了之。美國的庚款最有影響,胡適他們都是庚款留學生,3000多人。這些人都是一代精英。

高見
有一段曆史,我覺得現在研究的不多,就是黃安年先生出過一個《沉默的道釘》,原來的華工在美國給他們修鐵路,然後我讀過納什主編的120萬字的《我們人民》兩卷本美國史,還有是方納的《給我自由》兩卷本美國史。我注意到裏麵的一個細節:在美國的這些中國華工,其實受到了很嚴重的歧視。您怎麼看?
徐國琦:不僅是美國對華工歧視。整個從1882年,美國就通過排華法,在法律上歧視中國人。
《沉默的道釘》黃安年先生做的非常好,因為這一段就是中美兩國共有的曆史,它做出來了,當時中國人去給美國人建太平洋鐵路,鐵路富豪利蘭·斯坦福的財富是建立在中國鐵路工人的血汗、生命裏麵。但這一段美國的確是這麼多年來沒有承認過。

直到20世紀30年代,斯坦福大學中還有當年華工的後裔在工作
吉米·卡特當總統的時候,1979年表示感謝。但是這一段曆史,我一直說哥倫比亞大學欠中國人的,就是華工給它修鐵路。另外美國還有一個大學也欠中國人的,杜克大學。
杜克本人是賣煙草起家的,當時卷煙機發明之後,他就對助手說把我的地球儀拿來,他一看中國人口那麼多,如果讓中國人都抽煙的話,那他賺多少錢?他能賺無數的錢!於是就向中國賣煙草,中國人的生氣被他摧跨了對不對?但是從來沒有人研究過。
斯坦福大學最近才終於意識到它欠中國的,中美要聯合研究這個題目,現在正在收集資料,因為資料沒了,但現在資料很難收。
像杜克先生的那些財務,中國人應該找出來或者是中美學者去看,究竟在中國賺了多少錢?你是怎麼向中國人推銷煙草的?這個不用說壞或者判斷或者是要賠償,我把這段曆史給你還原過來,對不對?有很多的這種題目還要做。
《沉默的道釘》,黃安年先生做的非常好,但是資料現在還要進一步整理。因為要寫一部好的學術著作,需要很多資料,但是現在非常遺憾,這些工人絕大多數都是文盲,他們沒有留下什麼文字資料。
美國的文獻資料也從來不重視,因為美國人當時歧視他們,留下的記錄不多,現在一百多年之後,我們在想做這個題目,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斯坦福搞這個項目,因為我熟悉他們背景,現在很難做了,因為資料沒了。
資料沒了,你就沒法講一個完整的故事。你可以寫小說或者什麼的,但是不是曆史,所以黃安年先生那本書值得尊重。

高見
你自己做的中美共有的曆史是求同。現在中美學者很多人都在從事這個工作,你覺得它的主要困難是什麼?
徐國琦:實際上這個一直在做,在西方學者裏麵,某一個課題的研究很多,比如說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那都是大兵團作戰,各方人馬在寫。
它首先不強調你是中國學者、美國學者,看你有沒有資格寫,你是這方麵的專家你就可以寫,就像在2014年劍橋出了三卷版的一戰國際史,誰是這個題目的權威,你就寫,最後有幾十個國家的學者就參與了。
學術是不分國籍、不分宗教,就看你是不是這方麵的專家,你能不能勝任,你寫的東西是最尖端、最前沿、代表最新研究水平的。所以在這方麵實際上一直在做。
過去我們寫中美關係,比如說國內有一個陶文釗教授,他寫了三卷本的《中美關係史》,2004年是第一版嘛,現在又出了一個修訂本。
過去我們強調帝國主義侵略、強調中美對抗、強調中美分歧意識形態。像我剛才提到的中美關係,“共有的曆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就從這個角度給你講一段,中美兩國人民共同創造、共同影響、互相啟發的這一段曆史。這個可能有的是正麵、有的是負麵,但是無論如何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這種,“剪不斷,理還亂”,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比如說我再給你舉一個例子,就像體育。中國體育全運會,實際上跟基督教青年會有關係。基督教青年會1895年在天津設峰會,主要是美國人,然後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後來做過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的王正廷都是這裏麵來的,這就是體育,通過美國這個媒介過來。
中國人第一次參加奧運會是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後來1984年洛杉磯洛杉磯奧運會上拿的第一塊金牌。一些西方政要拒絕出席中國2008開幕式,小布什來了,還待了好幾天,這個就是“共有曆史”。

高見
最後一個問題,你手頭寫的第三部關於中國“共享的曆史”,這本書的內容大概是什麼?
徐國琦:這個就是我的“共有曆史”三部曲的最後一卷。第一卷是中美關係,第二卷是亞洲與大戰,都是共有。第三部,我想與國內學者像葛兆光、台灣中研院學者王明珂,還有日本神戶大學的王珂都在研究何為中國、何為中國人,因為他們這些人研究的主要是從中國談中國,我要從國際的角度,打破國家民族的概念,從上麵去看。
為什麼?就像一個人,如果你不跟別人打交道,你叫什麼?張三李四沒關係。因為你要跟外麵打交道。你是中國或者是中國人,所以你要跟其他國家要接觸,跟其他人接觸,你作為一個中國人或者中國。
所以我要從古至今梳理“中國”這個詞是怎麼來的。但現在我沒法告訴你內容,為什麼?因為我不知道答案,還正在做。做完了、研究做完了,想法成熟了,可能才有個答案,現在沒有答案。
因為真正做曆史的人,你不能先有答案,隻能做完了才有答案。我就算現在告訴你一個答案,也有可能會被推翻,因為我自己不知道,就像我當初做一戰華工,我沒有想到它的重要性,等我做完了,我才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在什麼地方。




























 粵公網安備 44140302000013號
粵公網安備 441403020000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