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水蘿卜和蘿卜幹,你喜歡哪一款?
沒吃到老家的水蘿卜,頗有些年頭了。
在安徽,每年立冬一過,家家都會從地裏剜回一堆大白菜,女人拿去水塘裏洗,男人把洗好的往家挑,在門前晾曬一到兩個太陽。晚上,女人就把白菜一棵棵往陶缸裏碼,碼一層撒一層鹽粒子,碼到最上麵,男人就會走上去光著腳丫用力踩,名曰“踩菜”。剛踩時,猶如踩在冰塊上,但踩著踩著,身子就會發熱,當腳下的菜踩踏的緊實並冒出鹽水泡沫時,也就踩好了,最後上壓一片石塊,再蓋上木蓋。這一缸菜裏往往還會放進一籃子洗得幹幹淨淨的削去根的新鮮白蘿卜。蘿卜不要太大,乒乓球大最佳,稍大一些,稍小一些也可,蘿卜放入量視缸的大小而定。
醃熟了的白蘿卜,我們這兒都叫水蘿卜,是不是因為從鹹菜水裏(鹹白菜被吃去一部分後,鹽水就漫上來,把菜淹住)撈上來的緣故,不得而知,大家都這麼叫,習以為常,沒有人去追究來由。
這種水蘿卜連皮吃起來,可謂色香味俱全,表皮杏黃,肉質鮮潤,從裏到外都香脆可口,能咬出嘎嘣脆的聲音,那聲音一聽,就會讓人食欲大增。可佐粥可下幹飯,可整個兒啃,可切成片或條狀吃,若在上麵澆些醋或抹點辣椒糊則更佳,與街上賣的鹹辣蘿卜條完全不同。講究些的,切成丁放些辣椒糊、或與鮮嫩的蒜葉炒著吃,都是很下飯的小菜。有時感覺嘴裏清淡無味,徒手從菜缸裏摳出水蘿卜,放清水裏擺擺,便往嘴裏塞,味道也是清爽得緊。
我心裏喜歡的水蘿卜不是那種大個兒的,而是比乒乓球還要小,捏在手裏模樣兒可愛,嚼在嘴裏,不用喝水拌飯,隻覺鹹香滿口。

這些家常便菜,農家小吃,雖不登大雅,不經意間鑽進人胃,卻使人沒齒難忘,時常縈繞心頭。
如果水蘿卜醃得多了,就還有另一種吃法。寒冷且有陽光的天氣裏,把水蘿卜撈出菜缸,用細長的軟竹簽或粗棉線穿成一串,彎成圈掛在屋簷下或門前的柴垛上曬,直到黃色的水蘿卜變成醬色、表皮幹癟起皺。收起來,裝入廣口瓶或搪瓷缸中,撒上八角茴香,過一陣子,便成了五香蘿卜幹。吃時切兩到四瓣,也可不切,喜辣的,可蘸辣椒糊,也有人從竹簽上直接扯下來,也不洗,就吃。其味獨特,鹹香且有咬勁,那是一種並不暴烈的陽光與冷風細細打磨出來的味道,無需其它的菜,下飯得很。
成家後,外出打工,這水蘿卜便成了記憶。一次在古鎮玩,無意間瞥見一家店裏有出售五香蘿卜幹與醬蘿卜的,說是民間特產,不禁大喜,這不就是年少時吃過的蘿卜幹?當即買了兩袋,迫不及待撕袋品嚐,卻大失所望,那記憶裏的味道怎麼也品咂不出。
我想,那記憶裏的味道,不完全是由於饑寒貧苦的日子之故吧。這袋裝的蘿卜幹,比較潮濕,帶些汁水,不似那屋簷下掛著的幹硬打皺、單純與簡樸,它是工廠裏批量產出的,加了佐料,還有味精、防腐劑,它沒有經曆那微暖的陽光與清冽的風,不是取法自然,它已經不是農家小菜了。

如今,一些農家菜成了都市人的追求,餐館也“與時俱進”,也有提供醃蘿卜片的,一片一片的浸著醋,色黃起脆,味道也佳,但它終究不是隻用鹽醃漬的“水蘿卜”,它是由種植在大棚裏的長條形的粗壯大蘿卜放了色素等製成的,是快餐時代化肥催生出的速成品,缺了天地靈氣,少了與白菜同缸,少了光陰的沉澱,終不是同一個味道。
現在,鄉村正在凋敝,土地被征,祖父輩們走的走,老的老,年輕些的都被趕進工廠,趕進小區,人們也不再為白菜蘿卜的采收、醃漬大費周章了。想吃鹹菜的,超市裏有,菜市場裏也有,一切都工業化程序化了,但那種把白菜和蘿卜一齊醃製的安徽製法,卻再沒有看到。很多年後,我依然很想吃到那樣的水蘿卜,以及那些田間地頭有著陽光味道的蘿卜幹,用它們蘸著辣椒糊,就著熱氣騰騰的幹飯或稀粥,心隨菜動,滋味十足。這大概就是我們回不去的鄉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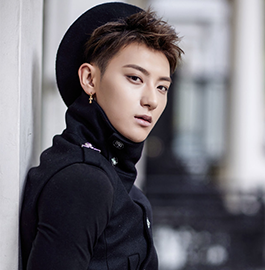






 粵公網安備 44140302000013號
粵公網安備 44140302000013號